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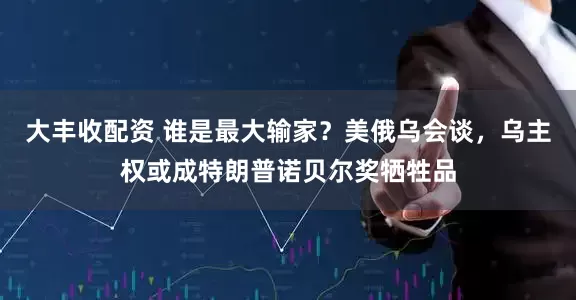
特朗普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渴望并非新鲜事。早在第一任期,他就曾公开抱怨:“我促成了一项协议,拯救了一个国家,却没得到诺贝尔和平奖。”虽然他没有指明具体是哪一国家,但这种不满和执念一直延续至今。挪威媒体披露,今年7月,特朗普甚至直接致电挪威财政部长延斯·斯托尔滕贝格,试探有关提名的可能。尽管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早在1月31日就已截止,特朗普依然不死心。他接连与普京举行峰会,在白宫热情款待泽连斯基,俨然一副“世界调停者”的姿态。
然而,专家直言,特朗普的外交方式过于浅显,将复杂的国际博弈简化为“校园斗殴”。他既缺乏对历史背景的敬畏,也欠缺解决长期争端所需的耐心与战略规划。
近几个月,特朗普频频以“和平缔造者”的身份亮相。2月份他与泽连斯基的首次会谈不欢而散,但8月18日再次会晤时,两人笑声不断,场面与此前形成鲜明对比。几天前,他刚刚在阿拉斯加与普京会谈,虽然未公布任何实质成果,却足以让外界联想到1938年的“慕尼黑会议”——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将捷克斯洛伐克割让给希特勒以换取和平。法国《世界报》评论称:特朗普并非新的张伯伦,他自认更像是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。
事实上,特朗普对“拿不到诺贝尔奖”的不满已多次公开化。去年10月,他在底特律竞选集会上高声抱怨:“如果我叫奥巴马,十秒钟就能拿到诺贝尔奖。他什么都没做,就得了奖。”今年6月,他又在“真相社交”上写道:“无论我做什么,都不会得诺贝尔和平奖,但所有人都清楚,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挪威媒体甚至报道,特朗普在与斯托尔滕贝格的电话中,不仅谈到关税,还直接提出“能否帮忙搞个诺贝尔奖”的问题。显然,他已把个人荣誉与外交议程深度绑定。
值得注意的是,特朗普并非孤军作战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7月访问白宫时,特意递交了一封推荐信,请求诺贝尔委员会将特朗普纳入候选人名单。巴基斯坦政府则在6月公开表示,特朗普调停印巴冲突,展现了“非凡的战略远见”,并正式提名他角逐诺贝尔奖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关系缓和阶段,也不约而同感谢特朗普的“介入”,两国领导人甚至向诺贝尔委员会发出“联合呼吁”。柬埔寨首相洪玛奈也声称,正是特朗普的介入,促成柬泰两国军队停火,因此他已提交提名。
然而,并非所有国家都买账。印度总理莫迪就明确表态:“世界上没有任何领导人曾要求印度停止军事行动。”一些国际问题学者也尖锐批评,特朗普声称“制造和平”,但其外交行为往往充满交易色彩。他提出吞并格陵兰岛、控制巴拿马运河,削减对非洲发展援助,甚至频繁威胁使用武力——这些举动与“和平”背道而驰。

白宫内部人士透露,特朗普喜欢自称“和平总统”。他之所以频繁涉足国际冲突,是因为坚信“快速和解”不仅能为自己赢得荣誉,还能带来实际经济收益。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例,双方在8月8日签署和平协议后,美国立刻与两国分别达成双边合作计划,重点推动基础设施和能源走廊开发。尤其是所谓的“赞格祖尔走廊”,特朗普宣称美国将拥有长达99年的开发协议。半岛电视台评价称,这不仅是和平协议,更是美国利益在高加索地区的新布局。
美国《政客》杂志则指出,特朗普推动国际协议的做法并非完全背离“美国优先”。在第一任期,他曾成功撮合《亚伯拉罕协议》,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多国关系正常化。不同的是,如今他更急于将这些“成就”包装为通向诺贝尔奖的敲门砖。
问题在于,特朗普的政治算盘很可能让乌克兰沦为牺牲品。在与普京会谈后,他并未提出任何实际制约措施,却将乌克兰问题继续悬而未决。欧洲舆论担忧,特朗普可能为了“制造一份和平协议”而迫使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让步。这与1938年张伯伦在慕尼黑的妥协极其相似。
如果真如外界担心那样,乌克兰的主权或将成为特朗普追逐诺贝尔奖路上的筹码,而这一代价,最终由乌克兰人民承担。
在特朗普的逻辑里,“和平”更多意味着政治资本与经济利益的交换。他一边高喊“美国优先”,一边在国际舞台扮演调停者,期待用几纸协议换来诺贝尔奖。然而,真正的和平从来不可能依靠短期交易完成。如果乌克兰真的被迫做出主权上的牺牲,谁才是这场“和平秀”背后最大的输家,答案似乎已经不言自明。
悦来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